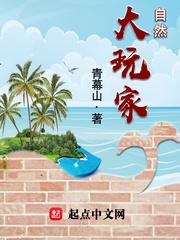电台小说网>近代史中国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 > 第 1 节 一种从未见过的盐(第1页)
第 1 节 一种从未见过的盐(第1页)
()
1913年那个初秋,陆阿伯在乔家浜弄堂的德成号油盐店里见到一种从没见过的盐。
那盐装在墨绿色的玻璃瓶里,倒出来却白如叠雪,一粒粒晶莹剔透,在日照下闪着光。陆阿伯思忖着:这东西怎么跟自家平常吃的盐不一样呢?家里的盐又粗又脏,一勺撒在锅里,跟碎砂子似的蹦出脆响。要是煮碗盐水,烧开了都有一层土灰浮在面上,在腾腾冒气的水涡里不停打转。
还是德成号的伙计告诉他:「这可是洋盐!好东西!别说腌肉腌菜了,拿它光拌饭吃都香,做菜放一小勺,小拧打了耳光也不肯放碗的。」
陆阿伯半信半疑:「个么我先前买的,也是天津长芦的盐哇,哪能就比不上了呢?」
伙计咧嘴一笑:「差远了好伐?人家洋人的盐,都是大工厂里生产的,哪能一样?」
喔唷,连吃的盐都是工厂造出来的。陆阿伯心里念叨着,提溜着一瓶洋盐出了油盐店,却迎面撞见一位西装革履、气质文雅的中年短发男人,操着外地口音,颇有礼貌地问他:「老伯,您买的这瓶盐多少钱?」
陆阿伯瞥了他一眼:「三十钱。」
那男人露出惊叹的脸色:「啊呀。这一瓶是一斤精盐,只要三十钱。我们自产的粗盐,一斤倒要六十钱。长此下去,莫说通商口岸,怕是内地都会偷卖这种走私洋盐!」
短发男人急忙迈开大步,奔回位于福州路的住处,取出纸笔开始伏案书写,直至深夜。第二天东方微白时,他便走出房门,将一封信件自邮局寄往背景,收件人是北洋政府的盐务署顾问景本白。
为何只是小小一瓶洋盐,便令这位中年男子如此焦虑?信件寄往的那个盐务署,又是什么来头呢?要揭开这一切,还必须要说到当时轰动中国的一件大事——善后大借款。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末代皇帝溥仪逊位,袁世凯借机掌控了半壁江山。而他所建立的政权所面对的,是一个革命派风起云涌,保皇派死而不僵的局面。特别是南方的革命党,始终对袁世凯的上位极为不满,各省举兵倒袁的呼声此起彼伏。袁世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铲除异己军事势力,便迫切需要一大笔经费。而当时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京的国库,都无比空虚。财政总长熊希龄清点国库后竟然发现,「南京库储仅余三万,北京倍之,不及六万」,这还没算上清政府多年来积欠的外债和赔款。
面对混乱的局面,素来和西方世界往来甚密的袁世凯决定向列强借款。英、美、法、德、俄、日六国组成的国际银行团(分别为汇丰、东方汇理、德华、华俄道胜、横滨正金,美国在威尔逊任职总统后退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控制中国财政的好机会,果断伸出了「援助」之手。经多次谈判,于1913年4月26日当晚,袁世凯绕开了国会,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五国银行团签署了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共计借款2500万英镑,年息5厘,按期限47年清还。
显而易见的是,五国银行团的借款是有着附带条件的,几乎可以用霸王条款来形容:这笔借款所围绕的一个重要核心,便是中国的盐税。
五国银行团在借款合同中明确声明今后中国的盐务收入、支出和管理都必须有洋会办参加;盐税和关税收入必须存储在五国银行团之银行,统归五国银行团执掌;至于盐税、关税收入偿清每期债款本息之后所剩下的余额,中国政府也不得私自动用,必须征得五国银行团同意才行。
为了确保盐税在自己掌控之下,五国银行团还要求中国政府整顿改良盐税征收,必须委派洋人来进行管理。为此,北洋政府才特意在财政部下成立了盐务署(原盐务筹备处),作为中央最高盐务行政监督机关,其下的盐务稽核总所和各级地方机关均聘用了洋员作为副职协助管理,权限很大。
所有的这一切条件,都意味着自善后大借款之后,中国的盐税主权彻底落入了洋人的手中。
熟悉中国历史的便知道,盐税对于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历朝历代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毋庸置疑是关乎国家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春秋时期管仲相齐,为助齐国称霸一方,便大兴盐铁之利,推行「官山海」政策,规定将盐资源归属于国家所有,并对食盐的专卖加以管理,此为中国盐政之始。如果说管仲的盐铁政策还是在生产上以官制为主,民制为辅,实行官收官运官销,那么秦商鞅所推行的食盐专卖制则是产运销均由国家控制,禁止私营。
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打击豪强商人和地方势力,并巩固大一统的新兴政权,刘彻采纳了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笼罗天下盐利归官,将盐商们占有的盐滩纷纷收归国有。煮盐、运盐、贩盐全部官营,史称「全部专卖制」。于是国库充实,也为他的征伐匈奴提供了经费来源。
隋代短暂出现过盐业无税的时期,到了唐代为了补贴财政,又逐步恢复了征收盐税。而宋代则实行行官商并卖制,将国家划分为沿海州郡的官卖区与内地州郡的通商区,并且从宋代开始后,海盐开始晒制,盐商需要用一种称为「引」的凭证来运输和销售食盐。
明代的盐政制度就更加完善了,不但全国盐政归属户部管理,还在各产盐大区设立了都转运盐使司,掌管一区盐政,并在盐场设场署负责监督盐的生产。对于销售则立「纲法」,一改过去官家收盐卖盐的传统,改由商人自主收卖,只是每年照册上旧数派行新引,纲册上无名的商人不得加入盐业运营,史称「商专卖制」。这种变革在当时虽然可称进步,但却使得行盐成了盐商专利的世业,渐渐导致了专商引岸独擅盐利的盐政弊端。
有清一代,专商引岸制度的弊端已然发展成为盐政领域的恶疾。所谓「引岸」,就是官府规定的盐场势力范围,比如长芦、山东、两淮、四川等。占据这些引岸的各大盐商,地盘壁垒森严,凭借官家给的凭证「引票」世代贩盐,外人一律不得染指。而且,任何居住在某一引岸地区的人民,只能购买属于该引岸的盐,如果擅自买了其他引岸的,就会以购买私盐罪论处。这种毫无自由度的销售制度严重违反市场规律,也让那些享受着垄断权的大盐商们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
对于买盐的百姓,大盐商们不但尅扣斤两,更是在所卖的盐里掺上沙土。一位长芦盐商曾经描述过操作手法:「每当原盐开包之后,总是往盐堆上泼热水或面汤。最恶劣的是掺土,甚至将例应倾弃不许食用的硝盐,以贱价收入,掺入大盐中售卖。」邹忠的《山东盐法志》也有载:「盐商运盐到岸,或八两算一斤,或九两算一斤,又或掺沙带水。」
粗盐中的一些杂质对人体有严重损害,比如硫酸钠、硫酸镁、氯化钡等。古代将含有这些金属杂质口感发苦的盐称为泻盐,一旦不慎误食轻者恶心呕吐、四肢麻木、腹泻腹痛,还会周身疲软乏力,俗称「软病」;重者肠胃痉挛、心跳加剧、血压升高,数日而亡。所以长期食用这样质量低劣的盐,会严重损害人的健康,但那些为富不仁、草菅人命的大盐商们自是不会在意的。
对于制盐的灶户们,大盐商们则极力打压从他们这里收盐的成本,使得原本就利润微薄的灶户们只能勉强糊口。他们自然也毫无任何购买先进生产工具改良制盐技术的动力。所以清代的制盐技术一直处于低下的水准,食盐质量大都很差,从手工到工业化的转型更是无从谈起。
辛亥革命之后,在盐业改革派先锋,《盐政杂志》主笔兼盐务署顾问景本白的大声呼吁下,各地改革盐政的呼声四起,四川、广州、福建等南方省份相继尝试了改革,然而他们大都是各自为政,采用的方法也仅是参照本省情况,无法推及至全国。另外,北洋政府的一些高官自身也和旧盐商存在利益纠葛。比如某任财政总长周学熙自身家族背景就是大淮商,手中握有食盐引票40余张,天然成为专商引岸制度的维护者。这样的人身居高位,对于盐业改革的阻碍可想而知。所以就连著名实业家张骞提出的《改革全国盐政计划书》,也终究因为触动了旧
()
体制的蛋糕,只能不了了之。
当袁世凯以盐税收入为担保的善后大借款签署后,负责改革中国盐税的是担任盐务稽核总所会办的英国人丁恩(RichardDane)。此公走马上任后,确实拿出了一套改革方案,促进了中国盐务管理的专业化,也打破了世袭大盐商长久以来的垄断,在部分地区逐步实现了食盐的自由贸易。可前门刚剿灭了虎,后门便引来了群狼——食盐贸易的宽松令西方出产的精盐也趁机而入,并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直接冲击着本土盐税的收入。
所以,虽然丁恩的改革不无成效,可袁世凯这种将盐政主权拱手交给西方人的行为,依然引发了民众强烈的不满。已经骑虎难下的袁世凯只能继续满足五国银行团的要求,决定组织一个考察团,前往欧洲考察盐专卖法,以及当地盐厂的先进制盐设备。
而在这批考察团人选之中,有一位叫作范旭东的化工领域专业人士。他,便是我们开头提到那位寄信给盐务署的中年男人。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相邻推荐:心机女主:轻松拿捏恋爱脑 人在吞噬,从娶妻开始无敌 美人豪横:倒霉女主的绝地反击 末世之我是避难所所长 股民张三,一个散户的百万之旅 全宗上下皆反派,卷王师妹杀穿天 深夜诡话:它在暗处注视着你 黑夜问白天:若我离去,后会无期 月亮回音:沉溺于他的柔情中 无咒:鬼神禁地,人性凶猛 婚姻围城里的算计 重生官场:开局迎娶副省长千金 高甜预警,这个男主不对劲 山月不知:你我皆为局中人 全职法师:次元之影 魔法蜜罐:你是银河赠与我的糖 妖夫娶亲:百无禁忌 我在三国经营田庄 搞笑日记,致曾来过的你 全民求生:我能萃炼万物精华